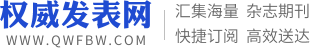|
[摘 要] 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阿城试图从社会批判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建立起文化思考与批判的维度。他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从历史到人生,还是从内在体验到表现形式,都表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尤其是在个体层面,阿城“寻根派”小说文本注重文化审美的现代性思考,其具体表现主要是超越政治阶级层面的“文化寻根”、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寻根”,以及感性力量与非理性因素的挖掘。
[关键词] 阿城;寻根;文化;审美;现代性
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阿城试图把眼光从现实移开,有意识地触及超越层面的话题,并从单一的社会批判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建立起文化思考与批判的维度。他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从历史到人生,还是从内在体验到表现形式,都表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尤其是在个体层面,阿城“寻根派”小说文本注重文化审美的现代性思考,跨越外在的社会制度形式而深入到现代个体的内在精神气质之中,不仅从理性,更从感性和非理性上探寻现代个体的存在状态与真实人性,并由此升华出对民族、生命、人的深刻思考。
一、超越政治阶级层面的“文化寻根”
回顾近代百年中国,我们一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发展问题,很多作家带着强烈的历史焦虑,迫切地参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讨论,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表现了作家们的功利启蒙心态。但相对于作家们的强烈革新愿望,其理论思维却是陈旧的,仍然用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来观察社会,对问题的看法表现出模式化与概念化的性质。就此可以说它们在深层内质上是“文革文学”的延续,缺乏文学本体的独立自足意识。
阿城则选择了另一种切入视角——文化的角度。对此,他曾经提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制约着人类”;“社会学当然是小说应该观照的层面,但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以及其它。”[1]文化这一“绝大的命题”,在阿城的小说创作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表现文化”,是他创作的自觉追求。因此,阿城的小说超越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将思考的视角直接指向了文化层面和人的存在价值,从而使其创作带上浓厚的文学审美现代性。
在《棋王》中,王一生的形象,可以说是传统民族文化的精神造型。阿城在王一生这个形象中,凝聚和概括了民族精神最深层的现实关系。王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顿顿饱就是福”。他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却是为了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下棋作为一种技艺,很难说能为人类创造什么,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却能帮助人们认识自己,激发起创造的自觉性。所以,王一生对棋艺的追求,正是人类无限的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人的聪明智慧可以达到如何的高度。这种不合作不随俗、高举慕远的形象,恰好与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景仰所尊崇的人格理想相契合。《树王》中的肖疙瘩当过人民解放军的侦察班长,立过战功,却被安排到偏远林场,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隐藏的坏蛋揪出来,但他却有一股坚定不移的民族忧患精神。他坐在巨大的树根上,以生命阻止李立们砍树,坚持要留一棵树,来“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2]。“老天爷”在这里既代表造化万物的自然力,又代表野蛮的破坏力,既是上帝,又是历史。留下一颗树“证明”的执着,给肖疙瘩的精神赋予了广阔的历史内涵和深层的文化意义。《孩子王》中的王七桶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哑巴,但他依然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着朴素的理想。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并且坚信儿子有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新生活,希望儿子有知识。“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3]在朦胧中能够将知识和力量联系起来,使他超越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庸俗观念,而表现出一种通向未来的现代意识。外形跟父亲一样笨拙的王福,突出的精神特征,就是自信认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会受到限制。认字也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王福的求知欲可谓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阿城的小说不是表面化地反映生活,不是仅仅从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角度,对现实真实作单向的探索和表层的描述,而是整体性地对人们的精神观念作综合性的考察和表现,在更广阔的覆盖面(文化)和更深远的层次(哲学)上思考民族历史和民族价值。其笔下出现的是负载着历史的重担却奋勇向前的几个普通人的精神和性格,但是却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从棋王、树王、孩子王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面对历史逆流的民族的尊严,民族的自信,民族的希望。可以说,“文化”这个具有丰富内涵与诗情的命题,赋予阿城小说以深厚蕴涵与审美意蕴。
二、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寻根”
阿城说:“丹青(注:画家陈丹青)要历史之真,我比较是要人性之真。”[4]确实如此。阿城小说人物的最有魅力之处,就是“人性之真”。他以冷峻客观的态度,书写人的纯粹的动物性以及人的丰富的社会性,书写“文明社会”遭受的种种污染,呈现出乡土的、蛮荒的、原生态的生命活力,彰显人的最本质的生活形态与生存本性。
阿城以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存形态表现“人性之真”。首先,他善写“衣食为本”。一是棋王王一生的吃相,那种执着的吃态描述得出神入化 ;二是知青们的蛇肉大餐,清蒸蛇肉的香气竟然掩盖了王一生与脚卵的具体对弈。阿城写饥饿感、写“吃”这种行为,写“食”的严肃性,其淋漓尽致与描写力度,是许多作家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食欲是人的最低层次的欲望,往往因其粗鄙的性质而被作家们忽略,而阿城却反其道而行之,将“食”的本能欲望从文学史的遮蔽中彰显出来。如此一来,人找回了基本的生命感觉,切身地体验了基本生存需求,由此感到了人的存在感,也就同时回到了“人”本身。这种荒原般的意象粗野中却见雅致,阿城以人物对“吃”的“虔诚”表达对基本生存的庄重态度,由此回归到了生命的价值与人性的永恒。
此外,阿城还善写畸形状态下的“性”。《遍地风流》短篇里,随处可见“性”的话题,书写了性压抑的男女、性的非常之态,让人感受到尴尬与荒谬。插队到太行山的女知青,在当地的天骂中领会到男女之事,便从此想象与期待自己的第一次“天骂”。(《天骂》)孙福从部队复员回到村里,与熟人打赌穿裙子的女知青是否穿了裤子,并忍不住去验证,结果被立即执行死刑。(《打赌》)一对同班的少男少女,在懵懂交往中情窦初开,女孩却因此被打致死,罪名竟是勾引腐蚀红卫兵,于是朦胧美好的“春梦”幻灭在“文革”中。(《春梦》)插队知青们在油灯下饶有兴致地讲起同性故事,在谈笑中寻找慰藉和乐趣。(《兔子》)爱情多么需要氛围,多么需要情调,多么需要文学的助兴,知青们因为青春年少和教化,都领会到了这一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时采菊?而且悠然?秋天嘛。”[5]知青们由此快乐,由此冲动,由此野合,由此还想刻一枚“山气日夕佳”的闲章。然而,“悠然”毁灭于残酷现实中——村妇与人“耍流氓”,丈夫弄个狗皮睡在坑下,一个男人每次付给两分钱;于是知青们揭发,吊打了那个女人;年底分红,村里每个劳动力分到六分钱。至此,“山气日夕佳”的闲章终究没有刻完。(《秋天》)阿城的笔下没有正常意义上的女性,没有浪漫想象的爱情。在他看来,本能欲望的压抑与禁锢不是通向人性自由王国的幸福之路。
阿城对所经历的历史重大事件敏感而又记忆深刻,但他并没有从历史的宏大层面入手,而是不惜挖掘历史纵深处多姿多彩的文化遗存,拣拾前辈作家们遗落的饼屑,开辟独特的表现领域。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突破了简单的价值判断,还原了生活的本真,呈现出丰富的立体性,表现了对人的本性的原始探索。
三、感性力量与非理性因素
宗教袪魅后,“现代人”失去了超越性秩序和神圣性意义的支撑,必然走向彼岸的世俗化。而世俗化表现在个体层面,则是以个体内在心性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人精神气质的生成,强调感性欲望的展现,遵循感性原则。感性力量和非理性因素成为了现在个体内在心性结构的本质性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感性和非理性长期受到压制的具体语境中,对感性力量与非理性因素的关注更加接近俗世中的现代个体存在,更能显示出文学现代性的审美意蕴。感性力量和非理性因素能否赋予现代个体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阿城以其小说做出了独特的体认。
阿城的小说尤其注意对人的生活本真的还原,注意对生命中感性力量和非理性因素的挖掘。其笔下的或人或事或景,贴近俗世俗景,充满志奇志怪的意趣,于朴野中透出几分灵动的色彩,可以说这正是阿城小说除理性意义之外的又一本质特征。
《遍地风流》诸短篇展现的是世俗的碎片,边关景色中蕴含的风流神采。独来独往的藏族骑手,在神秘宁静的气氛中,传达着一个民族在原始粗陋的生活方式里形成的强悍气质。(《峡谷》)粗犷豪放的汉子们,在闯荡人生中,诠释着张弛激烈的生命状态。(《溜索》)草原青年男女间打趣挑逗,在袒露的情感与舒展的性格中呈现出悠然自乐的生命情致。(《洗澡》)作者随记于阶级斗争惨烈的年代,寄予的情思,既在文里,更在文外。
面对一个荒谬畸形的时代,阿城以超脱的心态,一反当时普遍的沉重格调,沉浸于自己的经验世界中,饶有情致地记下与自己人生邂逅的青春点滴。他说过:“青春难写,还在于写者要成熟到能感觉感觉。理会到感觉,写出来的不是感觉,而是理会。感觉到感觉,写出来才会是感觉。”[6]不可否认,他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丰富的感觉与印象,他写出压抑的时代中难能可贵的一份青春的活力,凸显了历史真实中朴素美好的世俗面相。在这里,文明的理性和崇高被阿城以一种通脱的方式消解,这实际上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表达着创作主体独特的现代性体验。
四、小结
以上几点构成了阿城文化审美现代性的主要内容。虽然阿城小说与其他作家的“寻根”作品有相似之处,通过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分析,来对抗文学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窘境;通过对文化源头的追溯,找寻到人类的精神家园;通过获得文化意义,来实现民族自救,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它们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创作风貌。阿城超脱的心态,使得他能够在纷纭变化极不确定的社会生活中,拥有内心稳定和精神平衡的审美心理。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故事既源于现实人生之中,又超于现实人生之上,所传达出的是对世界人生的整体认知。或许,民族心灵的形式与现代意义的有机融合,正是阿城小说文化审美现代性形成的主要原因。
|